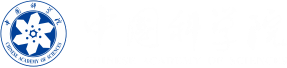我和我的兄弟
作者:吴衍庸
时间:2011-06-01
这是成都刚解放的一次记忆。我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参过军。在她的心中最为担心,最为疼爱的是我们最小的弟弟,我很理解,自古百姓爱么儿。我四弟吴衍康,那时仅十三、四岁。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18兵团进驻川西地区,60军担任成都警备任务,军文工队就住在我家(东玉龙街)隔壁不远的一座独院内。这里原是国民党军队一个师长叫黄敖的的私人住所。由于成都刚解放,文工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街头宣传,扭秧歌、打腰鼓、演话报剧,这些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当时,我弟弟和一些青少年学生受好奇心的驱使看热闹,不几天,就和文工队的领导和队员搞熟了,提出了想参加这个队伍,高高兴兴报了名。当时文工队的领导认为我弟弟年纪小,聪明,初中已读了几期,算是有些文化,经验试又会唱歌、跳舞,还喜绘画,就被录取了。我母亲开始也挺高兴,没多久驻军要离开成都远去北方,这时从没离开母亲一步的么儿,突然要随军而去,引起她心中不安、思想上开始动摇起来,日夜都在发愁,想要我去与解放军领导说情,想退出来。我和二弟得知后就给母亲做了不少工作,想法说服她。我首先说弟弟参军是自愿的,不能这样做,要相信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军爱人民,绝对信得过,参军很光荣。我又介绍一段我在学校被派参加拥军、助军的一项任务:成都解放后,西藏还没有解放,为了解放西藏,后勤上军粮是一个问题,这一任务落实到我们川大农化系上。农化系主任陈朝润是有名营养学家,他为解放军设计了一种叫“代饭粉”的营养配餐罐头。农化系在校内办起了简易食品加工厂,由班上同学参加,主要是生产蔬菜罐头和猪油罐头、腊肉、香肠也生产,“代饭粉”则在一家叫兴中农业公司的私人工厂生产。成都刚解放不久,那里敌情复杂,还遇到过在工厂处放黑枪的特务。一位解放军干部傍晚去厂,子弹打在他披着的棉大衣上,真危险。那时厂门均由解放军日夜值班,产品安全上由我们去的几位同学负责,产品生产过程,监督和质量验收,我参加了工作,得到党组织的信任,并且有机会与解放军驻厂干部和战士交上了朋友,与他们同吃同住。解放军和蔼可亲,同甘共苦、平等待人,相处得就像一家人。在我的眼里人民解放军与旧社会国民党的兵全然不一样。对国民党兵的印象有一句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谈了这些情况,母亲也有同感,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子弟兵,弟弟虽然年小,绝对放心得下,打消了母亲的顾虑,也不再提这回事。随后弟弟离开成都不久,又争取参加抗美援朝上了前线。在朝鲜期间700多个日子,杳无音信,母亲时时思念着远在朝鲜的四弟。我们在国内的几兄弟尽量安慰她,告诉她前线通信如何不便,以及部队的严格纪律,还有保密规定等等。其实在我心里同样忐忑不安。在这些日日夜夜,每逢节日,母亲都会受到当地驻军和居委会同志前来慰问,给母亲戴上了大红花,贴出光荣之家的喜报。我们几兄弟虽都不能在家共享母亲的喜悦之情,但也分享了给予的光荣。朝鲜战争结束后,四弟于一九五六年回家探亲见母亲。四弟穿上部队正规化新发的军官制服,在母亲面前敬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妈妈。母亲真没有认出这就是她思念着多年的儿子,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母亲50岁刚过,就重病高血压住进医院。我在重庆接到她病危的通知,向单位请假回到成都看望,假满后回重庆不久接到第二次病危通知,由于我将准备出差云南,未能再回家。这次母亲病危和去世,我和四弟都不在他身边尽孝。当得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我含泪无语,内心默默自慰,死不能复生,时光也不可倒流。半年之后,父亲得了癌症相继去世。往后的日子想到的是对父母的思念、感恩和愧疚,我怀着对党的爱,党就是我第二个母亲。
现在我四兄弟都健在,都是70—80岁以上的老人了。我1926年出生,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已退休20余年。二弟吴衍序1928年出生,退休前后在成都科大和川大教学,90年代曾受聘为美国南达科地州大学、万瀑大学、奥古斯坦那学院,太平洋路德大学讲学,被聘为各大学客座教授。三弟吴衍庥(吴休)1932年出生,1984年任北京画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90年代受聘为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客座教授,国内外知名画家。四弟吴衍康,1935年出生,退休前曾任成都市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四弟没有上过大学,却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进步很快,若父母亲在天有灵,将会含笑九泉,感谢党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