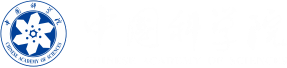《华西都市报》人工手绘两栖动物 建立首份最完善国情报告
时间:2019-08-27
费梁保存的老照相机。
1980年,费梁夫妇在九寨沟考察。
1984年,费梁和同伴在大凉山普雄考察。
野外考察条件十分艰苦。
科研人员行走在山林间。
原来没有照相机,动物图片全靠人工手绘。
手绘的青蛙图片。
年逾八十的费梁还在做科研。
费梁向记者介绍动物标本。
费梁的老伴叶昌媛正在忙着中国两栖动物志英文版的编撰。
普雄齿蟾。
世界上已知的动物种类有150万种,其中两栖动物有8084种。而在中国,两栖动物种类的记述数字为“454”。
作为茫茫大自然里“毫不起眼”的一族,两栖动物的生活似乎隐秘又低调。浅滩卵石夹缝中,潮湿茂密的草丛里,它们喜水的滋润,爱叶的荫蔽。
与这群不爱张扬的“精灵”们打交道,需要跋山涉水,弯腰探寻,看起来轻松实则费力。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费梁,带着团队走遍国内无数乡野林地、高山沟壑,建立起中国首个最完善的两栖动物“国情报告”。尽管“454”这个数字似乎那么微不足道,却花费了这些研究人员近一个甲子的时间。
如今已迈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和他那些大自然的朋友一样,不爱张扬,喜欢耕耘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尽管早已退休,但在研究所东侧办公楼二楼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费梁和老伴兼“战友”的叶昌媛每天仍相向而坐,继续琢磨着中国两栖动物志英文版的编撰。步履不停,笔耕不辍。
人物名片
费梁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馆员,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作为我国两栖动物学泰斗,他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信念坚定
我们国家的资源必须我们自己搞清楚
在对两栖动物的研究上,国外起码比国内早了近百年。当年那些游走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除了完成宗教任务,也顺便“窥探”着中国的动植物资源,扩充自己国家的研究成果。费梁认为,“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应该由我们自己搞清楚。
费梁强调,如今成果凝聚的不只他一个人的心血。
上世纪60年代初,费梁和叶昌媛先后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并被派遣到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在两栖动物研究领域堪称“祖师爷”的刘承钊和胡淑琴两位教授从事研究工作。
“在对两栖动物的研究上,国外起码比国内早了近百年。”费梁坦言,当年那些游走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除了完成宗教任务,也顺便“窥探”着中国的动植物资源,扩充自己国家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张白纸。
“外国人可以参与,但不能越俎代庖。”费梁从事两栖动物研究的信念简单且坚定,“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应该由我们自己搞清楚。”更重要的是,作为基础科学的一脉,两栖动物的研究对环境保护、防虫治虫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而最先专注于这个领域的,正是他的老师刘承钊。在上世纪30年代,刘承钊便开荒辟野,用脚步丈量着中国两栖动物科考的深度和广度。
哪些是陆栖类,哪些喜欢生活在近水,哪些又多活动于树上……在深进高山慢淌浅滩,下探农田上越冰川中,刘承钊将自己积累的经验告知费梁的同时,又指导着他去发现新的物种。 如进高原,对考察是种考验。1973年,费梁同青海生物研究所的一位同行闯入拉萨,翻过德姆拉山,试图验证在冰川湖旁的浅滩石下是否有栖息的生灵。“我们发现浅水里有蝌蚪时,就已经得出有成体存在的可能。但不敢蹲着找怕缺氧,就索性一屁股坐下,慢慢移开身边的石块看是否藏有目标。”
虽正值八月,但费梁和同伴仍裹着冬天的棉毛大衣。在几十平方米的范围,两人徒手翻了近两个小时竟未觉得冻手,最终发现了小而扁的西藏齿突蟾。
一步一个脚印里,“家底”逐渐积累。费梁向记者列举了一串数字:新中国成立前,国内两栖动物研究记录在册的物种没有过百,1961年加上有尾类这个数字也不过才跳至130多种,而如今已至454种。
艰苦探索
自带锅碗搞考察记录动物靠人工绘图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国内越来越多的两栖物种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等被记录和摸清,并对原来蛙属分类系统作出重大改变。由费梁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编目。
接过“祖师爷”的班后,费梁将大半的工作时间花在野外考察中,北行至冰城,南到过三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住行都成问题,费梁和研究人员们便自带锅、盘、碗、盏和铺盖卷辗转各地,一路上还得挑上十几个专门定制的铁皮标本箱,里面装着各类标本采集瓶以及工具。
费梁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在贵州考察时,当时条件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一斤大米,而野外考察非常费体力,于是他们向当地村民购买豌豆填肚子。要是没有蔬菜或嫌味道淡,就蘸一点从市场上买的辣椒面。
食不果腹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还不算什么,最让人心痛且难以克服的是当时设备落后,导致错失了很多记录动物生活形态的机会。当年没有照相机,记录各种动物形态全靠人工绘图。一旦捕捉到标本,绘图师王宜生便照着画下来。
不同于艺术创作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动物绘图必须按比例还原,以配合严谨的科学研究。绘图先勾勒大致轮廓,再细描各部分,最后层层上色。“有的青蛙背上成百上千的大小疙瘩形状都得完全一致,颜色填充后不仅要有光泽度还得立体。”费梁表示,按原比例完成一张青蛙科学绘图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彩色相机的面世,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当时费梁从课题经费中拿出5000多元购买了一台美能达相机,这台相机到2000年才光荣退休,至今被费老保存于干燥器内,崭新如故。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大至物种分类,小到涉及个体身体、眼睛、头等尺寸量度标准的完善,国内越来越多的两栖物种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等被记录和摸清,并对原来蛙属分类系统作出重大改变。由费梁牵头的“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编目,编著了《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国两栖动物彩色图鉴》等专著。这些成果获得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一次创举
发现浮蛙亚科
定义为第五个蝌蚪类型
费梁认为,科研成果还需要逐步完善和升级,前期“摸家底”构建起了形态特征的定性和定量判定标准,如今的研究则是向领域的各个方向扩展。“我们需要运用分子生物学更深入的研究剖析。”
如今,费老的研究辅助设备早就换成了数码相机。
费老把以毫米计的青蛙手掌骨架放在解剖镜下的玻片上,用相机对着解剖镜双目镜头一拍,就能得到一张高清的骨架图。
研究标本的取用也很方便。就在费老所在办公楼的正对面一层,就有一座目前亚洲最大的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馆内保存着10万余号标本,而大部分的标本,都经过费梁亲自鉴定、登记建档、分装和保管。
“相比于其他两栖类标本馆,这个馆内不仅对国内各种成体有详实的记录,而且还有不同发育阶段的蝌蚪标本。”费梁介绍,国内外想要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学者,一般都要先来这里查看。
费梁认为,这些科研成果还需要逐步完善和升级,前期“摸家底”构建起了形态特征的定性和定量判定标准,如今的研究则是向领域的各个方向扩展。
2004年,外国学者通过DNA研究,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印证了以尖舌浮蛙为代表的浮蛙属,可升级为一个新亚科或建立为一个新科。而这一结果证明费梁夫妇在十四年前依据形态学特征将浮蛙属提升为浮蛙亚科是正确的。“当时在实验室,从外表看采集的浮蛙标本与其他同类并无异样,解剖后才发现成体舌尖,而蝌蚪口部特殊且没有唇齿。”
就此,除各国学界原本公认的4个蝌蚪类型外,费梁夫妇发现和定义了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
“就这件事我不停思考过,之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两栖动物的形态和解剖,现在是需要与分子生物学相印证的。因为物种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演化,我们需要运用分子生物学更深入的研究剖析。”为此,费梁与南京师范大学周开亚教授商定联合培养第三代分子生物学研究人才,以扩大学科研究领域。
费梁介绍,在早期研究基础上,现如今两栖动物的研究已不止于分类、区系的调查,还有生态、行为、生理方面的研究,以及群落、类群、个体、组织、细胞等研究。
目前,成都生物研究所正在和俄罗斯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推进“一带一路”欧亚国家(地区)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与保护的合作研究,在助力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同时,也推动沿路区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幕后故事
从不吃蛙肉看见捕杀要劝阻
“这也是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一部分,涵盖了生态学、环境学、组织学等研究,对于相关技术科学和生产技术起着指导作用。”费梁举例,因为两栖动物的栖息离不开水源植被,迁徙能力弱,环境恶化会导致两栖动物减少,甚至绝灭。所以一个地区两栖动物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环境优劣的“晴雨表”,具有很强的环保指示性作用。
既然是和野外精灵们打交道,多年行走中,研究人员们也摸索出了一些相处之道。每次到了荒郊野岭,大家都会习惯性吆喝几声,弄出点动静,好像是给在暗处的“山大王”们知会一声,让它们暂时回避,以免互相打扰。 深夜露宿荒无人烟的野外,用厚油纸布或塑料薄膜支起的简易帐篷外,偶尔还会看到一些红眼睛绿眼睛的动物。“一次在二郎山还碰见了金钱豹,当时离我同事只有二十米远。”费梁回忆,尽管手中握有猎枪,但那位同事并未扣动扳机。“对峙”一会,金钱豹横跨过山窝,跑向另一座深山。
还有一次也在二郎山,车行至蜿蜒的大路时,前方突现野狼,沿着路跟着考察队的车小跑了一会。“只要你不去惊扰它们,一般情况下它们也不会主动来攻击人类。”在几十年的外出科考中,所幸费梁和其团队基本上没有遭受过野兽袭击的危险情况。或许是行走多年与自然界早已达成了某种和谐的默契,尊重和敬畏下也被自然界馈赠了幸运。
日常生活中,费梁从不勾选以青蛙肉为食材的菜肴,对于捕杀青蛙的行为,他更是看见一次劝阻一次。“首先它们是我的研究对象,我本就应该尊重它。再者其以捕食昆虫为生,能消治害虫,这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柴枫桔
记者手记
科考路上每一寸印记
都未曾被时间冲刷褪色
采访费老的当天,正值成都秋老虎发威之时。完成在办公室近两个小时的对话采访后,已快至正午。心想着让老人家休息一下,但他仍然精神抖擞地带着我们穿过被烈日烘烤的院坝,到标本馆进行下一轮拍摄。
下午3点过,本计划着去赶下一场采访的我们,又接到了费老的来电。“那台五千多的相机我从家里带来了,可以来拍。”想起上午采访时,我只不过是随口一提,而老人家却记挂于心。
对于我提出的大小问题,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家都细致作答。科考路上每一寸印记,都未曾被时间冲刷褪色,仍鲜活地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信手拈来。而也正是这些经历,让这位瘦小的老人显得活跃有趣。
因为体力的原因,费老如今多在室内伏案工作。最近的一次外出科考是在2015年,四川一高校的相关研究人员想去峨眉山找峰斑蛙,但不熟悉路,便邀请费老一起。因为只有他记得,峰斑蛙多栖息于峨眉后山,往零公里方向再走约两公里的时候上山就可寻到。“以前还有农民在山上种黄连,搭了棚子可留给我们作休息之地。只是现在山上的竹子窜了根,掩去了以前因打笋子而开辟的山路。”每一个不曾被人注意或忆起的细节,都被他咀嚼得有盐有味。
常常觉得如费老一样将毕生奉献于科研事业的人,犹如沉寂于海中的一叶扁舟,静观着日出日落,沉醉于你我都不曾仰望到的世界。而热爱和使命也让他们不觉孤独。尤其对于费老来说,幸得叶老的陪伴:那是紧握在地下的根,相触于云里的叶。
成都生物所知识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毛萍说,他常常上下班都看到这对老夫妇同行。夏天天气热太阳晒,费老就牵着叶老的手,缓缓绕过被炙烤的空地,顺着屋檐投下的阴凉处,向办公室方向走去。